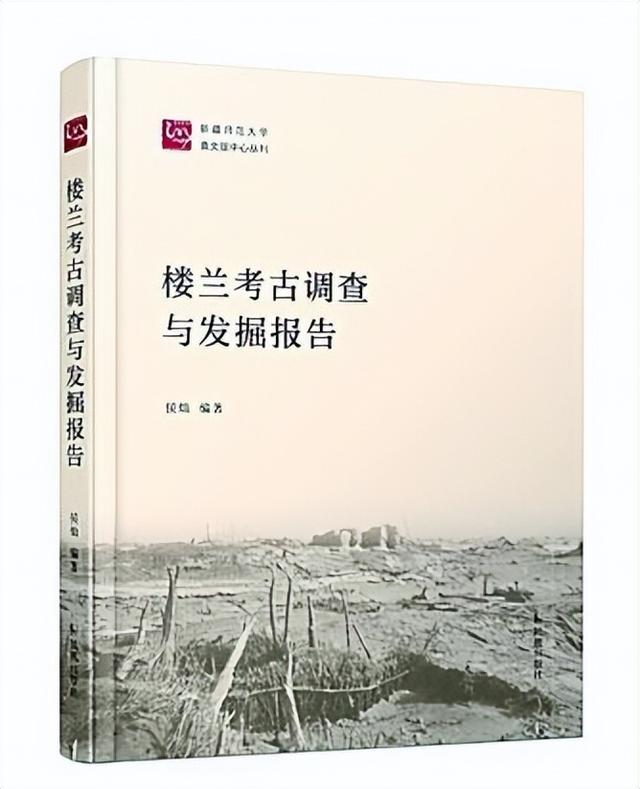
文章图片

大漠孤烟 , 长河落日 。 一度 , 人们在说起楼兰时 , 脑海里大概浮现出这样的景致 。 中华文明几千载 , 关于楼兰的记录 , 从汉代以来史不绝书 , 它出现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唐诗里 , 出现在“要斩楼兰三尺剑”的宋词里 , 却越来越成为一个神话 。 因为从魏晋以后 , 楼兰便难觅踪迹 。
直至20世纪初 ,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域考古中偶然发现了楼兰古城 , 这个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一千多年的楼兰 , 才再次回归 , 并成为国际焦点 。 1930年代 , 中国人黄文弼走进楼兰地区 , 却因罗布泊大水 , 而未能涉足古城;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 , 侯灿先生有幸深入楼兰 , 终于成为到达楼兰古城的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之一 。 日前 , 侯灿先生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在写就36年之后得以出版 。 如今 , 先生远去了 , 让我们跟随他的报告 , 去趟楼兰 。
走进楼兰
在有文字可考的典籍里 , 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贯通东西的绿洲王国 , 是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 但在魏晋之后 , 就真正只是一个神话、一段传说 。
1900年 , 斯文·赫定一行在考察罗布荒原时偶然闯入楼兰古城 , 打破了孔雀河东南16公里处持续千余年的寂静 。 长着一个高耸鼻子的斯文·赫定 , 嗅到了这里曾经的繁华 。 于是 , 在经过一番认真准备之后 , 斯文·赫定次年重返楼兰 。
在楼兰 , 斯文·赫定不能不说是喜笑颜开 , 他无拘无束 , 量长宽、捡铜币 , 简纸文书上的字他虽然不认识一个 , 但他知道那上面记载着古楼兰的过往 。 钱币、石制品、丝织品、简纸文书 , 斯文·赫定满载而归 。
此后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日本人橘瑞超也不甘示弱 , 他们从楼兰带走了他们能找到的宝贝 。
直到1930年代 , 中国人黄文弼才有机会进入楼兰地区 , 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记录了楼兰王国区域中的土垠遗址 , 但他还没有深入到楼兰古城 。 此时 , 在国际上 , 楼兰古城故事的讲述者 , 还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 ,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发言权 。
1979年 , 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侯灿先生有望打破这个局面 。 当年11月底12月初 , 他顶着严寒 , 乘汽车顺孔雀河北岸向东南行驶 。 此后 , 又徒步横跨干涸的孔雀河床 , 再穿越崎岖的雅丹地貌 , 终抵楼兰 。 这一趟行走 , 只为来年楼兰考古寻路 。
那一年 , 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 , 中日联合拍摄“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 , 其中由敦煌经楼兰至焉耆 , 荒无人烟的路段由中方单独拍摄 。 中央电视台便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作 , 组成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地区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 。
幸运之神眷顾了考古专业科班出身的侯灿 。 1979年11月的新疆 , 天寒地冻 , 物质条件和交通条件都相当艰苦 。 但敏感的职业习惯使侯灿明白 ,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 他和一行人不畏这些困难 , 万般珍惜这一次楼兰之旅 。
1980年3月27日 , 侯灿与新疆考古所的同事吐尔逊、吕国恩和邢开鼎 , 以及和硕县牧民宾拜 , 加上人民解放军89800部队负责给养、运输、驼队管理和劳动力提供的20多人 , 由前一年考察过的路线直接进驻楼兰 。 4月22日 , 大队人马完成任务后 , 从楼兰撤离 。
▲1980年4月 , 侯灿一行在楼兰考古 。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光明日报》
细数楼兰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撰成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 , 邑有城郭 , 临盐泽 。 ”显然 , 楼兰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城郭之国 。 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 , 途经楼兰 , 他在《佛国记》里记载 , 此地已是“上无飞鸟 , 下无走兽 , 遍望极目 , 欲求度处 , 则莫知所拟 。 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
往前的远古历史 , 无籍可考;东汉以后 , 史籍也不再见有楼兰的一言半辞 。 楼兰 , 从此隐没于历史之中 , 成为神秘之境 。
楼兰到底在哪里?发生过什么?当时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一探究竟 , 侯灿一行与古人“相逢”于孔雀河 , 寻找楼兰的历史瞬间 。
东经89°55′22″ , 北纬40°29′55″ , 走进楼兰遗址的侯灿一行 , 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核定了楼兰古城的具体位置: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南部 , 罗布泊的西北 , 西南直距若羌县城220公里 , 西北直距库尔勒市340公里 , 北距孔雀河最近点16公里 , 东距罗布泊岸28公里 。 在以往出版的斯文·赫定关于楼兰的论著中 , 也曾记载着当年他们深入楼兰测得的经纬度 , 而侯灿这一次的测量 , 更正了以往的多次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