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图片
《蝇王》 , 作者:[英]戈尔丁 , 译者:龚志成 ,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7月 。
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蝇王》早已设想过 ,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 , 即使一群儿童也可能建立起惊人的暴政 , 乃至残忍地杀死同伴 。 类似地 , 津巴多也毫不客气地指出 , 纳粹大屠杀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 , 我们看似和蔼的邻居也有可能成为杀人狂 。
然而“恶劣的环境”并非从天而降 。 它是如何生成的?或者 ,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 , “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 , 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在《鱿鱼游戏》中 , 系统的幕后黑手是看透人性幽暗的财阀 , 以及有着病态爱好的全球权贵——他们头戴面具 , 在酒池肉林中欣赏杀戮 。 这样的设定过于简单和脸谱化 , 也许便于普通观众理解剧情 , 却无益于深入揭示主题 。

文章图片
《鱿鱼游戏》剧照 。
游戏测试人性:
在虚拟世界里学会思考道德、警惕邪恶
值得指出的是 , 我们只需换一个视角便能发现 , 身为《鱿鱼游戏》观众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这场生存游戏的参与者 。 “希望看到更残忍的厮杀”、“两个只能活一个 , 迫切想知道那对夫妻档会怎么做” , 这些都是观剧时的常见心态 。 创作者利用了这种心态折射的幽暗 , 令观众照见自己人性中的局限 。
也许《鱿鱼游戏》还只是看破不说破 , 名导迈克尔·哈内克的《趣味游戏》则更直白地解释了上述这点 。 打破第四面墙的哈内克不断挑衅观众 , 让滥施暴力的凶手直接转过头来和观众对话 , 并通过任意改变剧情走向、几乎是嘲讽式地迫使观众承认自己对这种(尽管只存在于画面上的)暴力也是认可的 , 至少是欲拒还迎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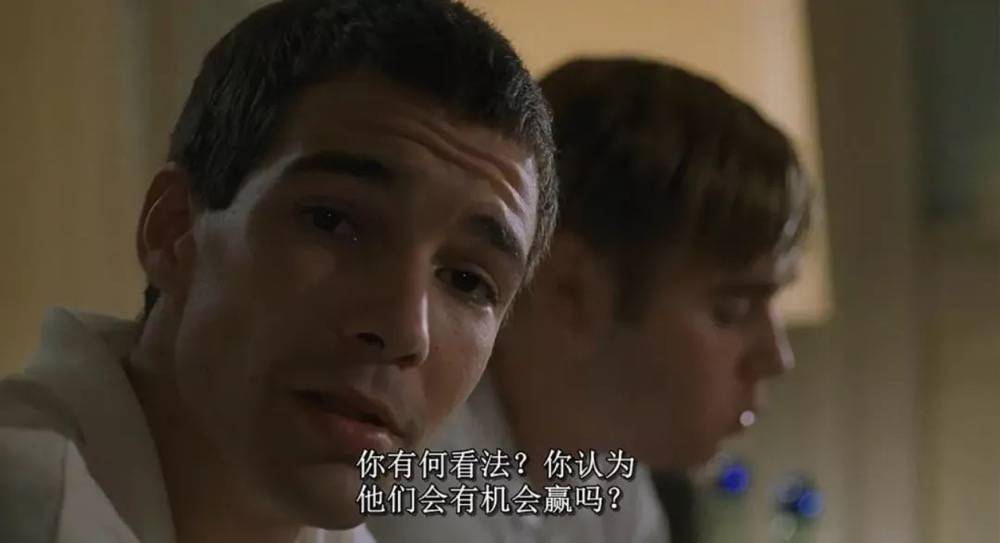
文章图片
《趣味游戏》剧照 , 剧中演员会打破“第四面墙”挑衅观众 。
比起《鱿鱼游戏》 , 《趣味游戏》与观众建立起更直接的互动 , 以此搭建了一个由影片和观众共同构成的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观众会感受到自己人性的底线一再被测试 。 不知是否因为激怒了包含影评人在内的观众 , 《趣味游戏》当年的票房相当糟糕 。
如果说大多数影视作品囿于传统形式 , 与受众的互动尚且有限 , 那么电子游戏的风行恰好补足了前者的这一弱点 。 由于其自带的交互属性 , 电子游戏为玩家体验各种系统开辟了一条通途 。 许多电子游戏都竞相在剧情和游戏方式中融入哲学思考 , 那些难以取舍、几近残酷的道德选择纷纷被丢到玩家面前 。 只要沉浸感做得出色 , 玩家就会被放置在类似成奇勋们的位置上 , 仿佛得到一张加入“鱿鱼游戏”的号码牌 。
推荐阅读
- 幻塔|《幻塔》原能信标藏哪里不容易被发现?大神想出无敌点位
- Among|吉田修平分享2021最爱独立游戏《暗影火炬城》上榜
- 评级|《老头环》ESRB评级定为17+:战斗场面太“狠”
- 幻塔|《幻塔》“虫洞”没法通关?选对正确BUFF,萌新也能打满24积分
- 幻想三国志5|《幻想三国志5》新DLC及系列游戏将于1月登陆Steam
- steam|Steam特惠:《港诡实录》新史低,多款年度大作半价甩卖
- 标准|《拳皇 15》PS4、PS5 国行版定价公布,299 元起
- 斗罗大陆|《斗罗大陆》被改编成评书,已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挂上钩了
- valorant|《剑侠世界3》刚开服1天,第一家族就被建立,网游教父亲自坐阵
- 武侠|《剑侠世界3》初体验:开服登顶APP Store的武侠网游有多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