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魏晋政治与族群︱中世的起点:五胡十六国( 二 )
由此看来 , 五胡十六国的开始 , 关键意味着胡族史作为中国史的主角登上了舞台 。 以匈奴为例 , 在比汉帝国的存在时间还要悠久的匈奴的最晚期 , 他们将皇帝制度和中国式官僚制为代表的中国王朝式的产物 , 引入了自己的国家体制 。 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特点 。 日本川本芳昭先生曾指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在五胡十六国之后 , 那些在汉、魏、晋的世界中曾被目之为“夷狄”的人群 , 已经变成了“中华” (川本芳昭《中華の崩壊と拡大》) 。 值得重视的是 , 这里判断“夷狄”“中华”的价值标准 , 是基于汉、魏、晋世界的认知 , 本文暂且称为汉帝国式的标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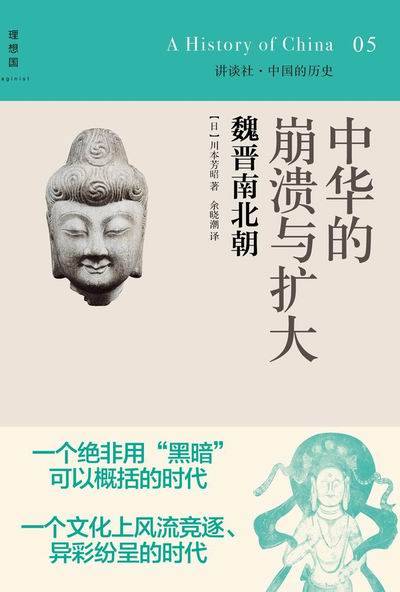
文章图片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但是 , 我们很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 , 简单地理解为是胡族的汉化 。 例如 , 张学锋先生认为 , 隋唐帝国的人与汉帝国的人 , 并不相同 , 应该称之为“隋唐人” 。 在汉代以后 , 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 , 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学锋《墓志所见北朝的民族融合》) 。 也就是说 ,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 胡汉通婚等现象 , 最终导致两者合为一体 , 是一股大的历史潮流 。 如果说胡族已经汉化 , 那么也可以说汉族已经被胡化 , 汉帝国式的胡汉分类 , 不再符合新时代的区分标准 。
说起唐代 , 其统治者并不单单是中国的皇帝 。 唐帝国的一些皇帝也被称作天可汗 , 唐在西方世界被称作“Tabghach”(=拓跋) 。 如果考虑到这些 , 不得不说唐代具有浓厚的胡化色彩(以汉帝国式的标准而论) 。 日本的杉山正明先生 , 把北魏以降的北朝诸国和隋唐帝国 , 总称为“拓跋国家” (杉山正明《游牧民眼中的世界史》) ,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的 。
不过 , 若将唐帝国与匈奴帝国或者突厥第一帝国那样的典型草原帝国相比 , 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 因此 , 以汉帝国式的标准来看的话 , 我们不得不承认 , 唐帝国无论与汉与胡 , 都无法直接划等号 。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显而易见的立场:“唐就是唐 。 ”将唐朝单纯纳入汉或者胡的范畴内 , 都是牵强的 。 而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 汉帝国式的族群标准 ,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 而如果基于唐王朝的“拓跋国家”特征 , 则汉唐间巨大变化的开端 , 无疑应当置于五胡十六国时代 。 正如内藤湖南所指出的那样 , 五胡十六国是“中世”的起点 。
二
如果说 ,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 , 胡族将中国式国家的诸要素纳入了自己的集团中 , 那么在此之前的魏晋时代 , 对胡族来说 , 则是割据中国内地的前一阶段 。 纵观魏晋时代 , 胡族们既保留了独自的部落组织 , 也吸收了中国式王朝的存在方式 。 那么 , 西晋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下的胡族的呢?从西晋朝廷发生的争论来看 , 当时对胡族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 。 接下来 , 我们就对此进行一番观察 。 由西晋官员江统提出的“徙戎论” , 是历史上著名的“异民族排斥论” 。 《晋书》卷五十六中记载的《徙戎论》 , 占据了《江统列传》绝大多数的篇幅 , 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中百万人口中 , 氐羌居其半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危险 , 二是匈奴的危险 。 在讲完徙戎论之后 , 《晋书·江统传》说:
帝不能用 。 未及十年 , 而夷狄乱华 , 时服其深识 。
此言赞扬了江统的先见之明 , 但从结果来看 , 他的徙戎论并未被采纳 。 从“帝不能用”一语可知 , 当时未能做到这一点 。 徙戎论未被采纳的理由之一 , 可能正是江统的意见在现实上难以实行 , 也可能是他的见解并非当时公认的绝对看法 。 事实上 , 西晋也不乏对匈奴抱有好感的官员 。
在西晋王朝面临一南一北之忧——即孙吴和秃发树机能两股军事力量时 , 曾有过是否让刘渊率领匈奴人出战的争议 。 《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记录了这次议论:
推荐阅读
- 蒂芬妮|中日韩3国99名练习生拼出道!选秀总监:节目不带政治色彩
- 政治学系|西瓜视频上线访谈节目《人生半场》:学者刘擎、脱口秀演员思文谈中年困局
- 民族|云会议|长周期政治论坛:天下与边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 叶璇圆|叶璇圆小时候梦想,《冼夫人传奇》出演女政治家
- 河西|窦融保据河西
- 党员|提升政治素养党课入耳更要“入心”
- 土木|魏晋六朝的建筑,为何被形容成“初发芙蓉”?
- 网信办|桥西区委网信办开展政治理论业务学习
- 丁霞|好消息,女排奥运冠军丁霞又多了一个身份标签,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 山东鲁能|这场比赛终于还是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鲁能这次惹怒了陈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