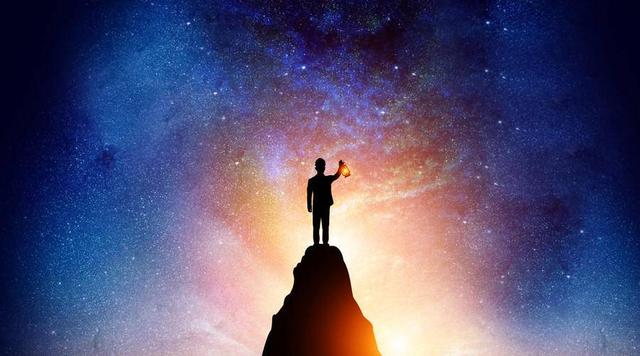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发生了并购重组的公司 , 并购前的公司股东、实控人在并购后的公司仍担任高管 , 但已经丧失了股东、实控人地位 。 该类人员在经营并购前公司中出现偷税漏税、做假账等违法违规情况 , 甚至这些人正是通过做假账把公司股价做高 ,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溢价将老公司股权售出 。 并购后做假账、偷税漏税等之前的违法行为被监管机构发现 , 该些人员仍在新公司担任高管 , 为了不被监管部门查处之前的违法行为而行贿 , 是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 , 原本应该是简单直接的个人行贿 。
但在实践中 , 有些司法机关将这类行为认定为了单位行贿 。 认定的法理逻辑是:被告人行贿是为了老公司股东的利益 , 体现了老公司的公司意志 , 是老公司的单位行贿;由于股权变更 , 新公司承继了老公司的法律人格 , 那么新公司就应该构成单位行贿 。 这样的逻辑既不符合单位行贿认定的裁判规则 , 是一种“借尸还魂”“移花接木”式的适用法律错误 。
单位行贿的认定标准当前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认定的共识是:一是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二是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实施(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 , 也就是说 , 以单位名义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单位);三是考虑是否体现了单位的意志 。
具体到单位行贿 , 《刑事审判参考》第1282号指导案例《被告单位成都主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王黎单位行贿案》提出认定单位犯罪的理由为“作为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 , 主观上系为单位谋取利益而实施行贿行为”“王黎没有绕开单位私自经营产品和截留货款 , 其本人获取利益系根据单位经营情况 , 通过分红、奖金等形式从公司支取 , 虽然王黎占有大部分股份 , 收益最大 , 但是 , 在法律上自然人的人格与单位是不同的 , 即便是同一个公司 , 也不能将两个不同主体混用 , 从而否认单位行为的性质” 。 可见 , 认定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 , 关键看行贿行为发生时体现了谁的意志、为了谁的利益、违法所得归谁所有 。 这是当前司法实践区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标准 。
已经不复存在的主体是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谁才能在行贿行为发生时有权体现公司的单位意志、为了单位利益是判断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核心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在行贿当时 , 老公司已经不复存在 。 担任过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控人 , 并不代表无论该企业最终被谁收购 , 都能永远代表该公司体现单位利益和意志的观点是没有任何逻辑和事实依托的 。 单位犯罪必须体现单位的意志、为了单位的利益 , 如果行贿行为发生的时候 , 公司已经实现股权变更 , 法定代表人、实控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新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实控人才能在此时有权利体现此时此刻公司的单位意志和利益 。
如果行贿当时 , 被告人个人与股东和实控人进行了协商、甚至个人名义召集过公司管理层会议 , 才可能形成单位意志 。
如果不顾股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实际 , 不顾被告人已经不能代表公司 , 行贿决策也没有向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控人汇报 , 被告人个人决定的行贿 , 体现不了新公司单位意志的事实 , 将行贿行为发生时已经不复存在的老公司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认为行贿行为体现的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老公司的利益 。 用借尸还魂、移花积木的手法 , 将行贿行为发生时 , 已经不复存在的老公司认定为单位行贿人 , 将原本没有体现行为时新公司利益和意志的个人行贿犯罪认定成了单位行贿 。 实际上就是在歪曲司法解释原意 , 错误适用法条 , 必然导致对被告自然人重罪轻判 。 毕竟单位行贿的法定最高刑是五年 , 而数额十分巨大的个人行贿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十九条规定:走私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或者其他资产重组后 , 原单位名称发生更改的 , 仍以原单位(名称)作为被告单位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企业犯罪后被合并应当如何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1998年11月18日)“人民检察院起诉时该犯罪企业已被合并到一个新企业的 , 仍应依法追究原犯罪企业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的刑事责任 。 人民法院审判时 , 对被告单位应列原犯罪企业名称 , 但注明已被并入新的企业 , 对被告单位所判处的罚金数额以其并入新的企业的财产及收益为限” 。
推荐阅读
- 上海一男子驾跑车冲撞五星级酒店大堂被抓,律师:或担刑责!
- 陈某醉驾,为何不追究刑事责任?
- 广东女子深夜与一堆男人吃夜宵,男友带人殴打对方被警方处理
- 女子信用卡透支未还被判五年罚五万。来看看什么样情况会追究刑责
- 江苏南通,一精神病人从四楼向下扔刀被判刑,网友:精神病人没伤着人也要罚?
- 司机疑因索债驾车撞向债务人,该如何处理?
- 广东深圳,男子因迷上赌博,卖掉孩子金锁偷拿孩子学费还赌债
- 广东广州,发生了一起暴力群殴事件。
- 9岁女童被13岁男孩追砍20刀,缝200余针险些丧命,警方:无法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