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首例人类猴痘病例1970年发生在中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 在随后的十年中仅报告了55例 。 该病毒虽然名为“猴痘” , 但并不是由猴子 , 而是由西非热带雨林中的松鼠携带的 , 一旦有人被这一主要宿主传染 ,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就开始了 。 它的症状与天花相似 , 也表现为脓疱疹 , 并且同样造成高死亡率 。 因为接种天花疫苗可以预防猴痘 ,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根除天花运动期间及其后 , 接种疫苗的人群没有风险 。 只出现了零星几个病例 ,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 然而 , 在天花疫苗接种已不再成为常规措施之后 , 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 。
1996 年 , 刚果暴发了猴痘疫情 , 疑似病例达511 例 。 其中42% 的病例是通过接触传播 , 由患者传染给家庭成员 , 这个比例高得可怕 。 它具备新发烈性传染病的所有特征 , 会在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的人群中迅速传播 。 虽然有一些疑似病例后来被诊断为水痘 , 但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进行实地研究 , 以监测该疾病的传播情况 , 这一疾病很可能起始于天花灭绝之处 。 考虑到这一点 , 也许我们在消灭任何病毒(最致命的外来病毒除外)之前都应该三思 。
眼下 , 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严重失衡 。 这也是最近“新”病毒感染增加的直接原因 。 只有我们恢复平衡 , 重新与周遭环境和谐相处 , 情况才会好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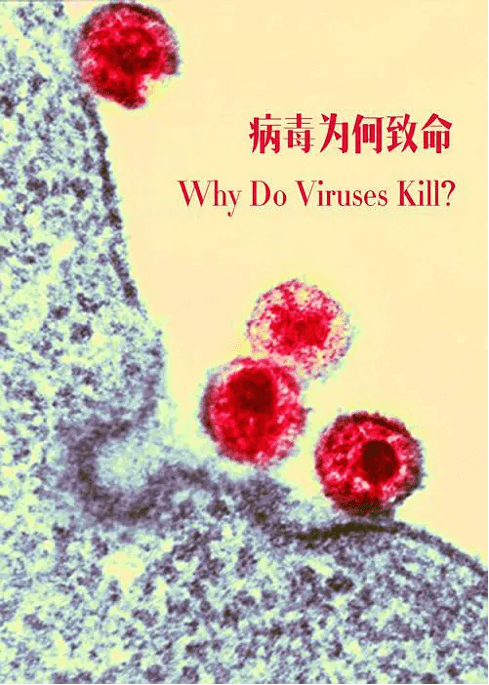
文章图片
纪录片《病毒为何致命》(2010)剧照 。
一万年前 , 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新的病毒感染 , 此后我们一直在努力控制它们 。 我们的免疫系统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感染 , 而感染也随之变得温和了 。 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 在适应期间 , 我们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主要是年轻人 。 康复的人获得了终身免疫 , 因此病毒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易感(年轻)人群 , 来维持它们的感染周期 。 而我们适应这种人口损失的方式就是不断增加族群的规模 , 确保部分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 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学以及疫苗的产生避免了大规模死亡 , 现在 , 我们的人口大爆炸再次将平衡打破 。 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六十亿 , 而且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 。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拓新的领地 , 从澳大利亚的内陆到南美洲的潘帕斯草原 , 再到非洲的热带雨林 。 在这些地方 , 我们又遇到了新的病毒和可怕的新疾病 。 因此 , 控制人口是打破这一循环的关键 。 与此同时 , 继续消灭致命性病毒和开发新的抗病毒药物应该可以确保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当然 , 除非是无意或有意释放致命病毒 。
推荐阅读
- 建设|这一次,我们用SASE为教育信息化建设保驾护航
- 最新消息|中围石油回应被看成中国石油:手续合法 我们看不错
- 标题|致我们的2021,所有奋斗终将闪耀
- 吴祖榕|上线 2 周年,用户数破 2 亿,腾讯会议和我们聊了聊背后的产品法则
- 植物|开放生物资源,保护多样性:我们为了生物安全的那些努力。
- nVIDIA|英伟达有可能将于2022年1月5日凌晨发布新一代RTX显卡
- jbhcfw|京东慧采适合什么样的企业入驻,我们公司合适么?
- 人脸信息|如何护住我们的“脸”
- 周建明|周建明: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基础科学研究?
- 感染病例|“奥密克戎”命名一个月 我们对它了解多少







